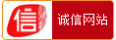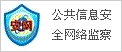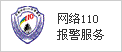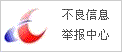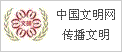作者:卢坡(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自春秋战国,国人即颇为重视“和”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以求天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追求“协和”“和合”,以求人和;在个人身心修养上,肯定“心广体胖”“和而不流”,以求心和。及至清代,“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桐城派兴起,延绵二百余年,学习与追随者遍及全国,甚至对日本与韩国文坛亦产生影响。桐城派顺应时代文化潮流,其发展演进、核心论点及文章风格都与“和”文化深度契合,体现出对于儒家“和”的高度认同。
最早对“和”文化展开讨论的是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国语·郑语》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史伯看来,“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则不能有所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关于“和”与“同”的差异,史伯进一步解释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不仅能区分“和”与“同”,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有“不同”的融入,又需要“和”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
“以和为贵”源出《论语》,《论语·学而》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和”本是就礼而言的,但又讲“小大由之”,即无论小事、大事都可以这样来实行,这就为从专言礼到泛言其他提供了阐释空间。脱离《论语》的语境,“以和为贵”就是“贵和”,后世更多地将“和”的对象引向人际关系,从而将“贵和”的对象固化和世俗化。实际上,“贵和”的对象并不限于人际关系,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多打上“贵和”的烙印。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姚鼐在为弟子陈仰韩时文作序时称赞道:“其为文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体和而正”的思想亦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源头活水。《论语·乡党》有“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记载,《子路》篇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又以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等儒家先贤强调的“正”,既有不偏不斜的意思,也有符合规范的深意。先贤在正与不正的对比中,有意为后世建构了一系列的典范。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桐城派作家多以儒者自居,其精神气质亦与儒者为近,如王昶以为姚鼐“蔼然孝弟,践履纯笃,有儒者气象”,姚莹以为“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姚鼐虽接人极和蔼,但义所不可,则不易所守,这从其与翁方纲、袁枚、钱大昕等人辩论中可见一斑,这又体现出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精神。可以说,桐城派植根于儒家文化沃土,儒家思想中的“和”文化更是深刻影响了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6日 13版)
责任编辑:秦亮











 浏览量:
123
浏览量: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