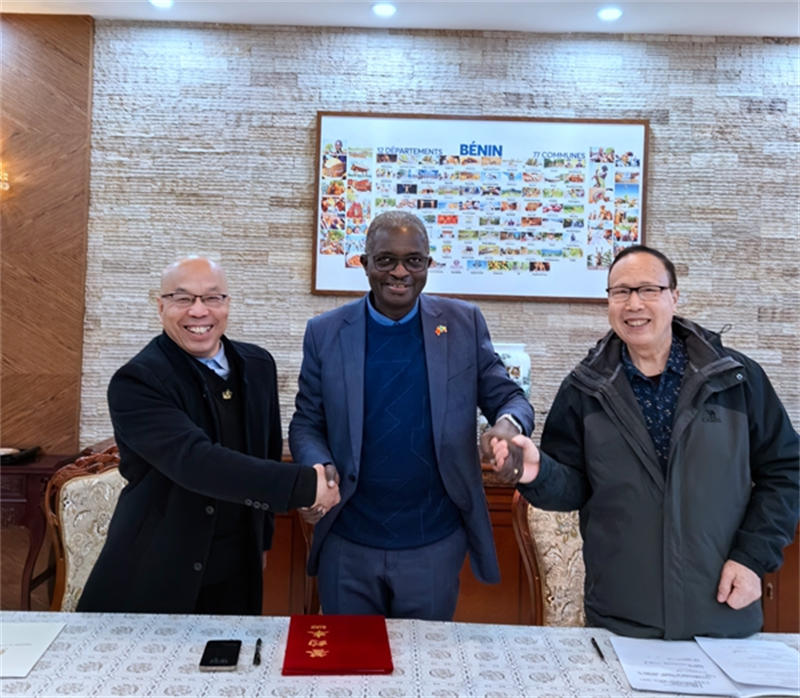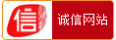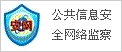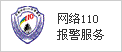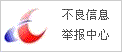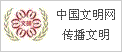作者:吴剑修(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庸》之“诚”,郑玄多训为“实”,朱子《中庸章句》则以“真实无妄”解之,然所指不尽相同。一方面,朱子将“诚”视作天地间实存的天理,如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循此理路,后世学者多视“诚”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朱子又将“诚”视作一种内不自欺,外不欺人的精神境界,一种与天理密合无间的成德状态,如朱子解“诚者,不勉而中”时说道:“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朱子以“真实”解“诚”,意在强调“诚”是天理之实然;以“无妄”解“诚”,则意在强调修道者对天理的把握。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即延续了朱子的观点,认为“诚是君子养心之道,诚又是天地四时的表现。天地四时的成就在于‘有常’,亦即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训诂的角度说,朱子解“诚”为“真实无妄”,算不得误释。一则,解“诚”为“实”本是常训。二则,《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也指向个体认知与外在事物的统一。但是,从对《中庸》之整体阐释的角度说,这种被后来学者广泛接受的解释,却将我们引入歧途,使得我们无法正确领会“诚”这一概念所传递出的真实意蕴。
对“诚”这一概念的看重,并非《中庸》所独有,先秦其他诸子对“诚”亦多有提及。赤塚忠、陈鼓应等学者认为《中庸》“诚”的概念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然正如徐复观所言,“老、庄所用的字语,都是几经发展演变而来,无一字语具有‘语源’的资格”(徐复观《〈中庸〉的地位问题》),我们其实很难确证“诚”这一概念是从道家发源的。折中论之,“诚”应属当时思想界所广泛存有的一种观念,为儒、道诸家所共尊,且诸家有关“诚”的论述,在概念指涉上也确实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中庸》在对“诚”的论述中,指出了“诚”的一个重要特质——诚能动化万物。如《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又说“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其二十六章又说“至诚”的代表便是天地,天地无心于万物,然其“诚”德之外发则又能化育万物。《孟子·离娄上》亦云:“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荀子·不苟》篇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都在强调“诚能动物”这一观念。不过,从《中庸》《孟子》《荀子》等关于“诚”的论述中,我们还不能准确推知“诚”的意涵。
除此之外,《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等相关篇章,也向我们展现了“诚能动物”这一观念。《韩诗外传》言:
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动而不偾,中心有不合者矣。
这个故事是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来源。诚心之现,而金石为之开,这是对“诚能动物”这一观念之极致化表达。根据故事所载,熊渠子“见其诚心”,其实是处于危险状态下的一种应激反应(虽然这种危险状态是其个体思维误认的结果)。在这种应激反应下,其内在潜能被激发出来。《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诚”是使“性”显现的条件。如果我们将个体潜能视为“性”的组成部分,那么“熊渠子射虎”的故事似可作“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之注脚。当然,仅凭这个故事,我们还是无法准确定位“诚”之意涵。而且,这个故事只是极端状态下“诚”心之发的案例,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如何能达到“诚”的境界,这个故事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启迪。
《韩诗外传》“熊渠子射石”的故事主角在《吕氏春秋·精通》篇中变成了“养由基”。《吕氏春秋·精通》篇有关“诚”的议论可使我们进一步切近对“诚”的理解:
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也。
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
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顺其理,诚乎牛也。
锺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锺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锺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的故事也向我们传递了“诚能动物”的观念,可知《精通》篇之“诚”与《中庸》之“诚”具有相同的意义指涉。据上所引“诚乎兕”、“诚乎马”、“诚乎牛”诸文,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诚”即是将注意力专注于某物。而且,有必要注意的是,“诚”所投射之物并非外物,而是心灵的内在显象,养由基所诚之“兕”,自始至终都只在养由基自身的内在图式中显现过,庖丁“三年而不见生牛”,亦与此同。如果说养由基“诚”心之发是源自对外在事物的误认,是一次偶然事件,那么伯乐“所见无非马”、庖丁“三年而不见生牛”,则是自主意识选择的结果。
据上《精通》篇之文,可知“诚”有“专一”之义。具体而言,“诚”即专心一致的精神状态。“诚”训“专一”,在训诂上也能得到解释。《白虎通·性情》篇云:“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玉篇》云:“壹,专壹也,诚也。”清代刘淇《助字辨略》亦云:“壹,专一,犹言诚也,实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擅,专也。按谓嫥壹也。《尔雅·释诂》‘亶,诚也,信也’,即此字。”此皆为“诚”“壹”二字义通之证。此外,孟琢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认为“‘壹’和‘诚’都有‘聚合—充实’的词源意象,‘诚’所体现的正是在它词源意义里涵盖的‘凝聚充实、专一不贰’的核心思想”(《对〈中庸〉中“诚”的文化内涵的历史阐释》),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维度。
另外,从《中庸》文本出发,亦可知“诚”有“专一”之义。《中庸》二十六章言:
故至诚无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为物不贰”即是对“诚”的解释。后文又引《诗经》“文王之德之纯”释“诚”,朱子言“纯,纯一不杂也”,其说可从。据《中庸》文本推之,可知“诚”有纯一、专一之义。但朱子又说“不贰,所以诚也”,并没有意识到“诚”本有“专壹不贰”之义,于是便错误地将“不贰”视为实现“诚”之境界的阶梯了。朱子如言“不贰,诚也”,则能切中《中庸》论“诚”之精义了。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1版)
责任编辑:李婧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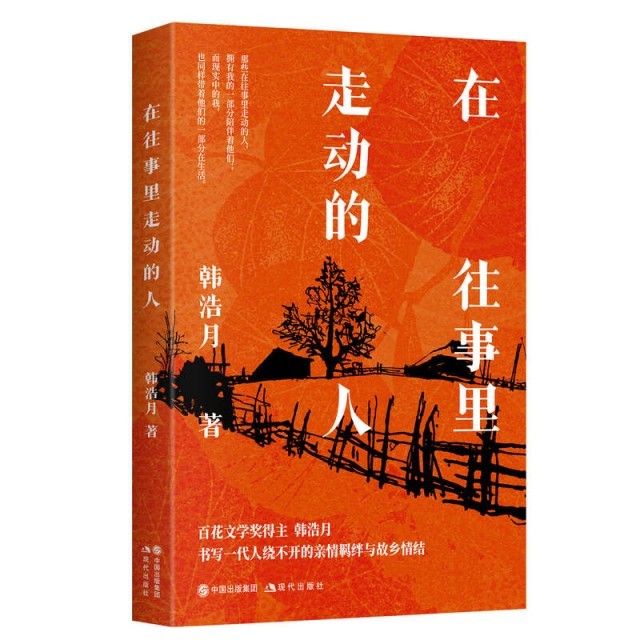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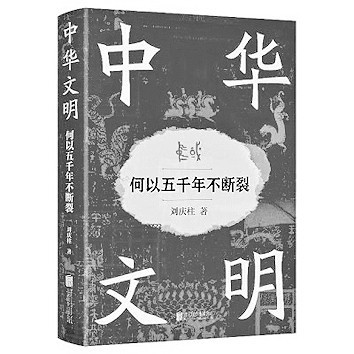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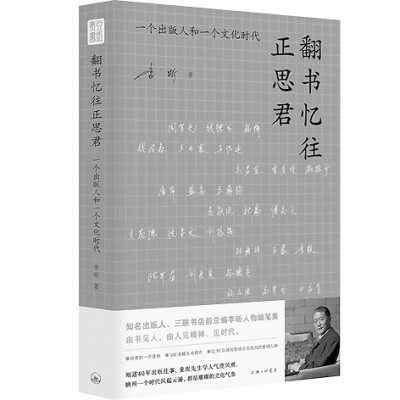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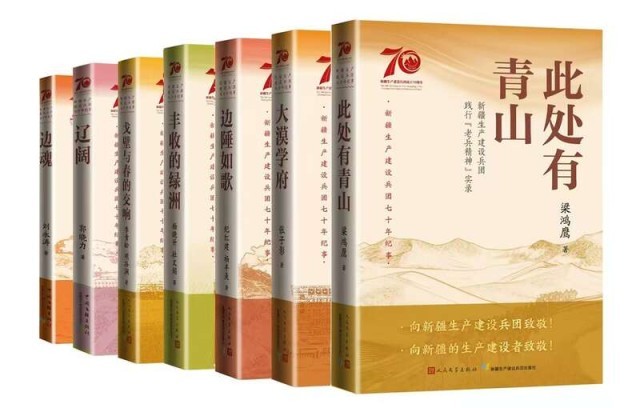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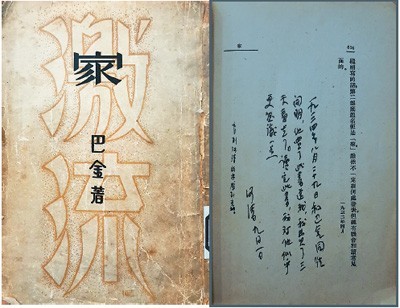


 浏览量:
87
浏览量: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