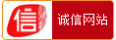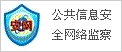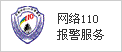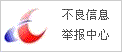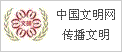时针指向22时。已埋首5个多小时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吴星潼,读完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最后一页。心潮澎湃的她走到窗边,抬头望向满天星斗。
满天星斗,正是该书作者苏秉琦六十年考古、半世纪传薪的生动写照。
苏秉琦,1909年10月生,新中国考古学主要奠基人、考古学“中国学派”倡导者、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创办人之一。学术生涯里,他创新性提出区系类型学说,认为中原地区只是中华文明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中华文明六大区系之一,并将新石器时期的中华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
“秉琦先生提出的文明观——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考古实际的深化。”他的学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说。
筚路蓝缕、青灯黄卷,拨开历史尘烟;一锹一铲、一担一篮,叩问缄默大地。1997年,苏秉琦逝世。但他的学说与精神,仿若中国考古学史上灼灼耀耀的“星斗”,始终指引后来人。毕生倾情教坛,为国培育栋梁,他的学生们,也在今日的学术科研星空中光芒闪耀,一如星斗。
星斗之光倾洒大地、无问东西,犹如先生育人极尽热诚,毫无门户之见。
20世纪50年代末,苏秉琦每周三去北大,常在未名湖北面的健斋休息。当时,严文明等一批年轻人常去请教,苏秉琦总是耐心指导、循循善诱。“各地考古人员来北京,多喜欢去看望苏先生,因为先生对所有找他的人从来一视同仁、坦诚以待,是大家公认的好导师。”多年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严文明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陈振裕,是苏秉琦亲自授课的最后一批本科生。他回忆:“先生从不搞门户派系,而是胸怀五湖四海,对素不相识的青年也一样热情接待、亲切交谈。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经常有人上门求教。”
20世纪80年代,湘潭大学教授易漫白想提高自己考古教学的质量却不得要领,便壮着胆子带着3名年轻教师来到苏秉琦家中求助。面对远道而来的求学者,苏秉琦连续四五天,每天下午讲几个小时课。易漫白事后才知道,那时先生患上了带状疱疹,疼痛难忍,却不曾透露丝毫。
“他爱学生。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这种爱超过了对自己孩子的爱。”苏秉琦长子苏恺之感慨。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家里买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每到周末,总有不少学生来家里看电视、聊天。苏秉琦十分欢迎,总是一脸和悦地和他们谈学术、唠家常。
“学生就是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成就了学生,就等于成就了自己。”苏秉琦说。
学生爱他、敬重他。有很多学生曾说,在他们心里,已经把先生当作父亲了。
1984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从美国访问回来,特地用省吃俭用结余下的生活费给先生买了一口电饭锅,希望老两口吃得方便些。
2013年,苏恺之去吉林大学拜会时任文学院副院长的赵宾福,发现在赵宾福办公室的醒目位置,挂着父亲1988年参加他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的合影。
星斗之光深邃辽远、奥妙无穷,犹如先生治学严谨勤勉,深深影响一代代学子。
1965年,苏秉琦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篇划时代巨作”。西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孙庆伟认为,先生对仰韶文化的突破性认识,固然得益于他对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材料的系统整理,也得益于他对类型学方法炉火纯青的运用,但最为关键的,是他对该项研究意义的清楚定位,即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一步”。
这是苏秉琦个人的“顿悟”,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顿悟”。孙庆伟说:“从1934年在斗鸡台初涉考古,到1965年的这番‘顿悟’,先生所悟出的,正是考古学著史之道。只有通过对不同区域古文化的分子水平研究,考古学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历史,才能真正完成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升华。”
考古学科极重视野外实习。苏秉琦将培养田野考古人才作为重要目标,凡能参与的,他一定前往。
带队实习,苏秉琦屡屡展露自己“摸陶片”的绝活儿——从野外实习现场的众多陶片中,精准挑出四类八种,又很快排出演化序列。学生们直呼“神了”,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一些学生轻视“摸陶片”、不重基本功的偏见。
星斗之光深情恒久、照人前行,犹如先生为人民治学、为祖国奉献,不慕虚名,不改初心。
苏恺之回忆,父亲第一次委派他“做大人的事”,便是去买1950年2月16日出版的《进步日报》。那一天,苏秉琦专门写了短信,并将其和报纸一同寄给各地友人。
“报上登的是父亲写的一篇短文,《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13岁的我有些疑惑,父亲早已出了那么多成果,一篇小文章登报,怎会那么高兴?”长大后,苏恺之才明白,这篇小文,饱含着父亲多年来对新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憧憬,答案全在“人民的事业”五个字上。
这篇文章,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开展考古大众化工作的经典之作。
20世纪90年代,步入暮年的苏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国史前史”,身体力行诠释着“世界的中国”与“最大的文章”。他对学科使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考古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这是它的从业者的天职。”
1994年,85岁的苏秉琦在回顾一生学术道路时,发出“六十年圆一梦”的感慨——把考古学建设成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
于学术孜孜以求,于名利却淡泊处之。
苏秉琦一生不重官衔,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外,未担任任何社会职务,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布衣教授”;更不喜在电视上露面、自许“不是社会名流”。从不刻意追求“著述等身”的他,成果质量很高,如恒星高悬,光辉万丈。
“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古史研究的贡献不是在一个‘点’上的突破,也不是在一个‘面’上的成功,而是贡献了一整个全新的古史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邵望平说。
“谈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不能不讲苏秉琦教授。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其实是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向前走。”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说。
当年春风仍在,依旧煦拂四方。满天星斗,在穹隆深处熠熠闪亮,在学术星空永世流光。
(记者 晋浩天)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浏览量:
2383
浏览量:
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