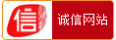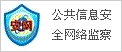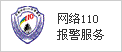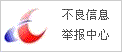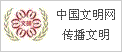张怡微 受访者供图

《哀眠》
张怡微作为写作者的名字,第一次见诸媒体,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对00后来说已经有些陌生的词,在80后、90后眼中代表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张怡微在2004年获得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那已经不是大赛的风口浪尖时期,那一年,她17岁。
从文学起步的《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再到《四合如意》和最新出版的《哀眠》,张怡微18年来的代表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她的笔下,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处境、婚姻思索、移民命运……都拥有了新的面向与轮廓。
张怡微的学术专著则大多和《西游记》有关,包括《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情关西游》等——除了作家,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意写作专业的副教授。
作家进高校教书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张怡微只是觉得,两个身份一叠加,生活就被“摧毁”了,导致“一直在工作”。“也许我的爱好是上班,但有时也爱好或者说憧憬,能放个大假。”张怡微说。
中青报·中青网:《哀眠》是一个短篇小说集,现在写短篇的青年作家似乎不多,你是喜欢这个体量的小说吗?
张怡微:其实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多,只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想要获得权威的肯定,短篇小说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径。也正因如此,写短篇无“利”可图,更有一些纯粹的特质。
我并不能说喜欢这个体量,而是我有正式工作,高校“青年教师”的本职就极其繁重,我一年中能够筹措的时间,只够写作和发表2-3个短篇小说。我入职6年,差不多就完成了《四合如意》和《哀眠》。
当然,我自己很喜欢阅读短篇小说,同样是因为时间稀缺。除了上课时会用到的书,我已很久没有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我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压力,以便不要沉浸于阅读的舒适区。比如,最近我接了一个重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活动,争分夺秒地在重新翻阅、理解和认识长篇的结构、人物的出场,以及副线的构建。
我很喜欢读小说,无论长短。
中青报·中青网:有人评价你的小说是“世情小说”,你怎么理解“世情”?
张怡微:这是一个评论家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关注,不过作家不太可能围绕某个人的看法来写作。从文学史的角度,世情小说也不是一个纯粹褒义的词。我觉得我的小说确实比较通俗,我自己也是通俗小说的爱好者,不然也不会通过《西游记》安身立命,完成博士论文,还给大学生上《西游记》导读课。
世道人情中,只要是说得清楚的感情,其实都没有写作的必要性。文学应该照亮的是复杂的感情,所谓“难言之隐”。但没有必要,不代表要回避它、完全不去书写它,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识别、提炼情感背后的深意。这就涉及我们怎么理解人、理解社会结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都比较关注自己身边的普通人,所以我没有写英雄,甚至没有写出一个比自己聪明的人。我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写普通人的婚姻和离散。我现在37岁了,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欲望,心中会涌起新的写作需要。
在收入《四合如意》的短篇《字字双》《四合如意》里,在今年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中篇《失稳》里,其实都有一些夹缝中人。例如,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学校教书的老师,他们有时会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边界的人群,也会将自己置于这种交界处。
例如《字字双》中的安栗,她是做老年人情欲研究的,她可以用第二语言来回避许多中国文化中讨论情欲的尴尬,但她还是要面对家人,来诉说她花费大量精力留学、求职,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有一个刹那,母亲和舅舅们为了争取拆迁的房子在闹事,她不知自己应该加入还是当观察者。这些瞬间,是我喜欢捕捉的,也是我比较熟悉的。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为什么会关注老年人群体?
张怡微:我也许写了一些老年题材的小说,但从数量上来说,还是写少年、青年的更多。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年轻”,我甚至已经没有办法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我们都会老。我最近也和朋友们一起在调研一家养老护理机构,采访护工。但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少,大量的聊天和采访基本都浮于表面。关注老年人群体,不是我以作家的身份在关注,而是我以一个对未来生活有推理欲望的研究者,希望参与、优化社会配置做一些微小的努力。
我们采访过一位护工阿姨,很有意思。她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市中心工作,先生在上海郊区当门卫,新冠疫情3年,他们3个人都在上海,但没有见过面。她有抖音,她会躲在养老院的厕所里录歌,她在抖音里美颜过的脸,和真实生活中的完全不同。她们的照护工作非常辛苦,但她们有自己的方法逃逸到虚拟世界中。
我觉得现代传播的各种媒介或者技术,是城市生活中的现实主义。现在互联网非常下沉,那些网络的用户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对偶像的看法,我们在学校里待着是无法推测的。老人不会因为我们设计他们过什么生活,他们就过什么生活。
护工阿姨说,只有你们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问题,我们农村没有这个养老的概念。
中青报·中青网:那在新媒体时代,爱情、亲情、友情这些古老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张怡微:在很多人看来,我算是一个重度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我用微博推荐我的书、我喜欢的书,推荐我的学生,推荐我们的专业。但是我很少会在社交媒体谈论爱情、亲情和友情。我只在论文、课程、专栏里,就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戏剧作品,来讨论这些话题。我也不展示和更新与情感有关的任何生活。我觉得社交媒体是一个公共场域,它只是一部分的我、工作中的我。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会就合影、就@的对象做文章,蛮可笑的。亲密关系的难点,并不在于用什么媒介、什么频率交流;它在于,在重大决策时、利益可能受损时,我们该怎么谈判,该怎么预判风险。相处一直很好的人,有可能与我想法不一致,正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我并肩度过人生下半程。
在这些关键节点上,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大,反而是古老的力量影响更大。当然时代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话题,会给我们在灰度地带来更多的叙事空间。
我对传播学一直很有兴趣。本科时进了复旦哲学系,想转去传播系,他们没要我。这些小的情怀像种子一样,一直埋藏于我的精神生活中,可能到最近几年发挥了一些文学面向上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虚构的故事中感觉有你自己的影子,你的个人成长经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怡微:多多少少有一些我看世界的眼光,但如果说是我自己的影子,那其实我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能力都不如我,我也过得比她们好——这对写作来说,是很遗憾的。困顿是生活日常,虚构写作却是可以借助可能的条件,活出生机、走出困局的。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对我知识性的影响微乎其微。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们家的书,是我从零到数千本自己买起来的。但我30岁以前经历的许多生活问题,例如家庭解体、亲眷矛盾、独生子女政策、出版合约纠纷等,当然是构建“我成为我”的经历,帮助我看到自己相对顺遂的成长道路中看不到的那些人。她们中,很多是弱势的人、被看漏的人——我是有可能成为她们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赵超】











 浏览量:
7176
浏览量:
7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