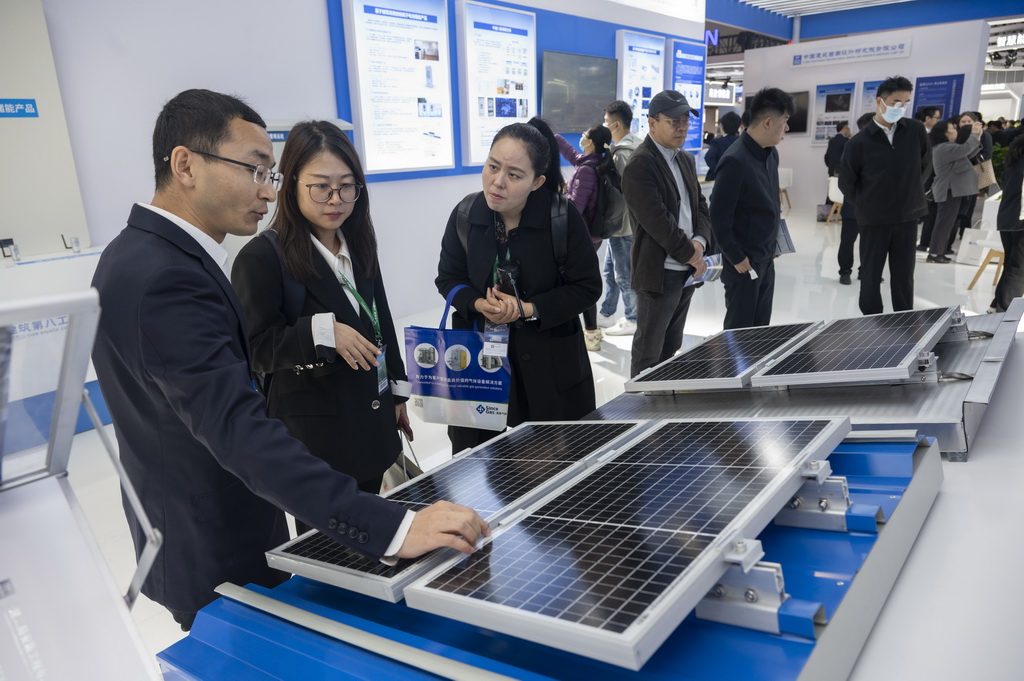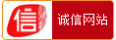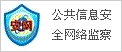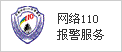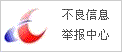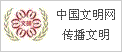谈及游记,《徐霞客游记》,其文既有山石的嶙峋之态,又具流水的清润之音。而《阿来游记》有翠墨烟霞之美,宛如一幅幅展现川、藏、云、贵、甘、青等地民俗风情与山光水色的长轴画卷,神秘且富有风情,传递出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洞察与哲思。
阿来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深入民间,汲取教益,接纳口传文学与自然文化的滋养。其笔下的山川湖泊、大地河流、古迹遗址、草滩荒漠,连同人文地理和历史脉络,皆被赋予灵魂。他对民族文化的熟稔与尊重令人敬仰,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文化的多元与珍贵。阅读这部游记,仿佛与阿来一同漫步于深情且神秘的高原,沉醉在每一处风景的雄浑与秀丽之中。
有良知,怀揣赤子之心
此前读过《西高地行记》。两部书,多有交叉之处。
回顾《西高地行记》的阅读记录,当时在散文《果洛的山与河》的空白处写下:是内心敬畏与崇拜孕化出的文字。在“孕化”下方又写了“韵化”二字,大概是感受到其文字如音律般美妙。
《阿来游记》置于枕边,某个清晨,4点刚过,天色大亮,睡眼惺忪的我再次翻开《果洛的山与河》,仍能逐字逐句沉浸其中。这次我未在空白的页面写下一字,是我对优美文字、对怀有赤子之心的阿来、对雪山湖泊大地的敬畏吧。如果说“蓝色的鸢尾花是他思绪化成的青烟(阿来语)”,那么也可以说,他的文字就是他用深情汇聚成的清冽的溪流。
散文《果洛的山与河》中描写的黄河,使人感慨万千。那清澈的黄河,辫状的黄河,如孔雀般美丽的黄河。它灌溉了无数田畴村庄,翻越了众多电站大坝,滋润了大片干涸大地,接纳了诸多污秽糟粕,改变了自身的颜色,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或许,它早已忘却了自己在草原上清澈的模样和藏语的名字。一条河,为了世间的繁华,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更新着自己。就在这个清晨,我对内心早已敬仰万分的黄河有了全新的认知。
此前读野鹰《草与沙》,知道正是藏民对雪山、大地、河流的虔诚与信仰,才有了黄河如今的面貌。他们从不破坏,唯有敬畏。取用,只为所需,绝无贪图。野鹰与阿来一样,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的敬畏深植于骨血之中,这是内心的崇拜与敬畏孕化出的文字,绝非阿来仅凭肉身写下的文字。他的文字输出源于灵魂,源于敬畏,源于虔诚,源于信仰,源于中华民族奔腾不息的血液。时有惊涛拍岸,时有细浪呢喃,时有春风拂面,时有秋光斑斓,文辞之美着实令人欣喜,说翠墨烟霞之美,不足以盛赞,更非溢美之词。
当阳光洒进窗台,当我睁开双眼看到世界的瞬间,便邂逅了如此清澈纯净的文字。它圣洁、虔诚,影响着我,改变着我,鼓舞着我,引领我向善向美。
有担当,肩负时代使命
如果认为《阿来游记》仅仅是展现自然与智慧的文字,那绝非阿来本意。在他的文字中,能读到关于现实的隐忧,也可以说,阿来的游记承载着时代的厚重意义。评论家谢有顺说:“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文学脱离了世俗的庸常和浅薄,真正地立了起来。”
首先,对于“游记”这一文学体裁,阿来有着深刻独到的认知。当下,游记体散文面临危机,常见的问题是只见作者的姿态,却不见书写对象的真切呈现。例如,写“我看梨花”,许多人重点落在“我看”,而阿来认为重点应是“梨花”。前者是一种姿态,后者才是真正的呈现与书写对象。写物,首先要让物得以清晰展现,而后涉笔其他,方有可信的依托。阿来还指出:“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生境中,自然会呈现不同的情态与意涵。若不考虑主客观环境,仅套用主要植根于中原情境的传统审美言说方式,就等于自行取消了书写的意义。”阿来以这种敏锐的视角去发现一片土地,用行走告诉读者,在行程中要有全新的体察与认知,这无疑是最为关键且最具生命力的。
倘若将“梨花”视为呈现,把“我看”当作姿态,那么我认为“阿来式”的这种理论完全能够运用到文学评论中。就阅读来讲,呈现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文本的客观展现,需要有耐心,并且读得细致、用心,毕竟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后还必须对文本进行深度挖掘、思考,才会有“我看”的姿态。这种姿态,方能呈现出“我”,展现出独属于“我看”的深刻之见。
那么再回归到“呈现”层面。我们完全能够从阅读文本里探寻到阿来呈现的方式,这主要涵盖四种:立体、整体、角度、历史(文献或者典籍)。阿来文本中的那些历史文献,绝非单纯的引用,以增添游记的文学效应与美感,而是蕴含着一种佐证,或者说是针对地域文化、生活、生态等方面的追根溯源。往小处讲,这是职业使然。往大处说,则是家国情怀。
其次,社会发展进程中,古老文化传承的缺失、摒弃,以及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令人忧心忡忡。人类向自然索取时,更应认识自然、学习自然、呵护自然,避免伤害自然。从自然鸟兽草木山川河流的生命中获取灵感,发现与理解自然之规律。问道名山大川,日有所行,夜有所思,每有所见,其目的是一个“从外向内”的启发、领悟、接受自然教化的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人与人、转向人的内心的生命关系,并为我们人类所用。那些关于理想与现实,纯真与困境,文明与落后的对峙,作家很多文字都有发人深省的表达。
在《古老的开犁礼》中,作家发自肺腑地写道:“这个时代,水泥在生长,在高歌猛进,自然在退缩,自然之美在退缩,退缩时不但不敢抗议,不敢诘问,而且是带着深深的愧疚之感。”其实是痛,又不能发出呻吟,内心无言以对,无颜以对。这是不是对文明与代价的追问与反省?主动与被动,无疑都会对原有的生态文化造成损伤。“我们正日渐廓清文化的来路,却还不清楚文化去向未来的路径与方向,我相信这个答案只能从民间新生活中那些自然的萌芽中得到启发,能够找到吗?我不肯定,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了寻找。”足见阿来的游记并非以游为乐趣,以记为目的,其实是对民族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作广泛而独立的考察,是他内心的立场与价值的体现,也是游记的厚重意义所在。
有情怀,心系故乡山水
我不禁想起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确,阿来是土生土长的藏民之子,如今功成名就,只因离开了故乡,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可他的爱却始终扎根在那里,在那片青葱的土地上繁茂生长。他曾多次沐浴于霞光夜色,将脸贴着大地,鼻息间满是泥土的馨香与淡淡的草香,“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在反复阅读《上升的大地》之后,愈发能感受到那深沉的情感就隐藏在字里行间。作家用了一连串的“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递进句式,直至最后写道:“就是这样,我从山下尘土飞扬的灼热夏天进入了山上明丽的春天。身前身后,草丛中,树林里,鸟儿们歌唱得何其欢快啊!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谢命运让我如此轻易地就体悟到了无边的幸福。”这一连串的重复用语,无疑是一连串的刻骨铭心的深情,是对故土、对生命的炽热深情!温情中流淌着诗意,那一株株开着宝塔状花蕾的马先蒿,那黄中带蓝紫色的野菊花,那连缀成片的鸢尾花,都化作了“苍茫随思远,消散逐烟微”的悠悠思念。只因出了这峡口,便是心心念念的家乡马尔康了。
遗憾的是,在阿来的游记中没有看到故乡的美食给予阿来肉身与灵魂的慰藉。唯此一段。我想把这百余字的童年美食记忆摘抄下来,以飨读者:
小路穿过一片阴湿的小树林时,我突然在林子中看到了一种属于春季的花朵:毛杓兰。这种袋状的紫色花朵勾起了我一些亲切的童年回忆。童年时代,小孩们在山上放羊的时候,总是四处去采摘这种花朵。然后,把揉好的酥油糌粑一点点灌进花朵的袋子里,放在小火上慢慢烧烤。最后,剥掉已经全然变干烧焦的花皮,花朵的馨香全部浸进了小小的一团糌粑里,那是一种童年游戏中烹制出来的美食。
这段文字让我想起了我许久未曾归返的故乡,在那片安静的土地埋葬着我的母亲,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的祖父,埋葬着我的至爱至亲,我的根就在那里。幼小的童年,是故乡的阳光、雨露、空气、食物,慰藉着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离开故土,回望故乡的时候,是故乡的记忆再一次以安抚的姿态浮现在脑海,一次又一次慰藉着我们僵滞的灵魂。作为离开故乡多年的我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故乡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是走出嶙峋现实、走入自己内心的另一种活法。
喜欢阿来的文字,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映照出了我童年的山村生活。故乡对于作家阿来而言,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归处,也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藏。他一踏上那片土地,内心便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深情。他的游记,诸多篇章可谓字字含情、句句蕴情、页页传情、篇篇陈情。阿来,是真正与雪山、草地、高原融为一体的人。这哪里是寻常的游记,分明是对故乡、故土、故人的一次深情回望。
阿来的文字,有着厚重的史学修养,兼具浓郁的人文情怀。既展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文化的热爱,又揭示了文化在现实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以及内心对那片故土的隐忧,引人深思,令人敬仰。
责任编辑:张建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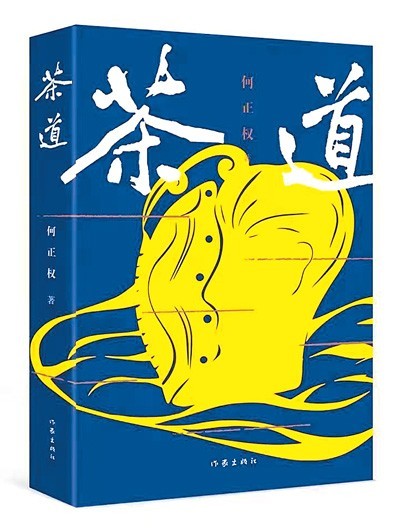





 浏览量:
147
浏览量: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