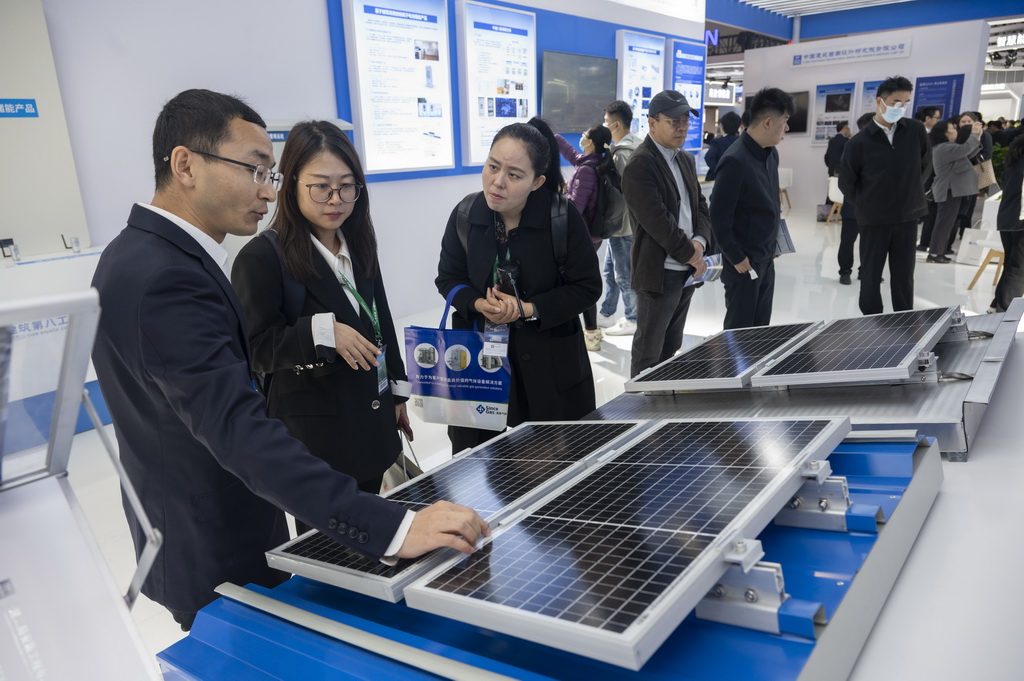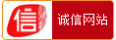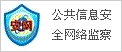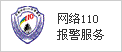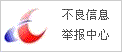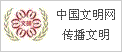《过渡劳动》。作者供图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抵抗一种压力,那就是把外卖骑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孙萍在《过渡劳动》导论中说。孙萍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描述了这一职业群体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展示他们在城市之中如候鸟般来去匆匆的生活。
《过渡劳动》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带着行动派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从而提出“过渡劳动”这一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孙萍直言:“每天奔跑在街头巷尾的骑手会让我产生一种数据唾手可得的乐观。”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街上“捕捉”骑手并不容易。“他们像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极易受到惊吓。静止的时候你扑上去,他们会立马躲开或者逃跑。”
为了完成对于外卖骑手的调查,拿到真实的数据,孙萍自己去送外卖。她说,感受特别深的是“因为受到工作的限制,新手去跑外卖就是‘菜鸡’”。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没办法去跑外卖做专送骑手,只能做众包骑手。
“像我这样的众包骑手非常‘菜鸡’,第一是抢不到单子,好单子很快就会被专送骑手抢走,剩在抢单大堂里面的单子几乎都是‘取经单’,所谓‘取经单’就是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送到的那种单子。”孙萍说。
她有一次抢到的“取经单”需要爬楼梯,手里还提着两个西瓜。“抢到这种单子,可能未来一两个小时就只能送这单了。”
“一个专送的骑手,一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协调七八个订单。”孙萍说,她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的劳动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
谈到自己为何去送外卖,孙萍直言:“在田野调查中,我慢慢学会了如何体验和理解这个江湖。有时候是我的嗅觉、触觉、听觉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有时候是我理解空间、地方、流动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
在书中,孙萍采用了自下而上的展开方式,试图将话语的主体性重新归还给个体劳动者,从他们的视角窥探过渡劳动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引发的社会影响。
谈到这本学术著作对于青年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对这个世界充满迷茫和疑惑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周边的人在经历什么,以及他们的这种经历和自我的勾连,这种有智慧的做法可能给自己带来破局之道。”
“送外卖让我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
“数字职业研究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学生雷津皓谈到自己送外卖的经历时说:“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外卖系统在引诱你,让你一步步上瘾。”2023年3月,孙萍说:“你能不能跑跑外卖,做一做田野调查?”雷津皓刚好很感兴趣。
“我跑的第一单外卖非常轻松,取餐的地方到送餐的地方只有100米。”雷津皓接下的第二单,也是100多米,稍微远一点点,第三单再远一点,大概就是900米。“这个系统会一步一步引诱你去迷恋上这种劳动。”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
在一个小区,顾客要求把外卖放到外卖柜里。但雷津皓翻来覆去在手机里就是找不到外卖柜的打开方式,眼看要超时,刚好来了一个外卖员,他赶紧过去求助。
跑外卖之前,雷津皓还“跟车”跑过外卖。2023年11月2日,雷津皓在交给孙萍的田野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上车后,鑫哥第一句话是,“我这单可远啊!”“远不怕,就怕不远。”我回答说。
正说着一股推背感袭来。鑫哥骑车的感觉比我上次跟车可凶太多了,用横冲直撞来形容完全不过分。
我坐在后面胆战心惊,唯恐出意外。接下来,更让我胆战心惊的事情来了,鑫哥在机动车道开始摆弄手机,他在抢单……
“在跟车和送外卖的过程中,我总是把过程记录得很细,因为孙老师要求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个现场。”雷津皓说,那段时间,他和几个“数字职业研究小组”的同学每天外出跟车,每天记录和骑手们一起送外卖的各种“现场”。
雷津皓说:“《过渡劳动》让我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当二维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也会和孙老师去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却不着边际的学术论断。”
戴锦华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同学和老师去送外卖,而是他们能够在多层次上深入到这样一个新的生产和生活的劳动状态中去,所以,我真是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敬意。”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说:“《过渡劳动》一书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劳动者的理解与尊重,在这个旧有结构与新技术权力绞合的时代,释放出一种温暖的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高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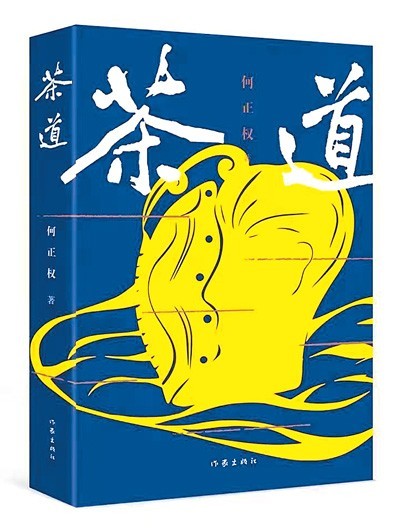




 浏览量:
67
浏览量:
67